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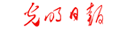
|
|||

|
|||
|
|||
|
【千字说文之“来往”】 周兴嗣《千字文》第五句“寒来暑往”,将“来”“往”两个表示位移的动词与“寒”“暑”两个时间名词连缀,组合成精妙的二元对仗结构,不仅声韵和谐,更在意义上错综交叠,体现出季节更替的秩序感,以简洁的语言构建出古人的时空认知体系。“寒”和“暑”代表四季中的两极,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寒暑”连用表示的是一整个太阳年。“来”与“往”则表示空间位移的双向过程,也代表万物运动的周期性变化。声韵方面,平声的“寒”“来”与上声的“暑”“往”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节奏。该句将抽象的时间推移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温度与物候变迁,充分体现出古人“取象比类”的智慧,实现了知识传播与思维启蒙的双重教育目标。 “来”字甲骨文象禾麦之形,《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中的“来”就表示本义“禾麦”。“来”被假借表往来之“来”,指由别处到此处,见《诗·小雅·采薇》“我行不来”,毛传“来,至也”。甲骨文添加与行进义相关的“夂”旁另造“麥(麦)”字,表示往来之“来”。由于往来之“来”的使用频率极高,鸠占鹊巢,反使专为“来”造的本字“麥”转而承担了表禾麦的记词职能。战国楚文字在“来”的基础上添加“止”旁,强化行来义,秦文字中仍沿用“来”字。“来”常与其他动词连用,表示做完某事后归来,如商代晚期宰甫卣“王来狩自豆麓”,意为商王从豆麓狩猎归来;也可以表示到说话人所在地做某事,如《左传》多见“来会”“来盟”等。除此之外,“来”也可以表示使动用法的招徕义,如《吕氏春秋·不侵》“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后分化出“徕”字专门表示此义,现代汉语也常见“招徕顾客”“以广招徕”的表达。除到来、招徕义外,“来”在空间上的物理趋近与时间上的未然将至形成认知同构,引申出“将来”义,催生了“来年”“来日”“来世”等表达。这体现了汉语词义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关联性引申,类似情况还有“间”由“空间缝隙”引申指“时间间隔”,“交”由“空间交会”引申指“时代交替”,“际”由“空间边际”引申指“时间节点”等。此外,“前”与“后”、“上”与“下”、“来”与“往”等,则通过身体经验构建起完整的时空坐标体系,形成了从“空间位移”到“时间流动”的意象图式。这种引申规律说明,人们总是以具象的空间经验为认知基点,通过隐喻投射的方式建构抽象的时间概念,在词语的多维语义网络中镌刻着民族思维对时空一体的独特理解。 “往”字的甲骨文,是从止、王声的形声字,西周金文延续了这种写法,直到春秋时期才在【图片①】字基础上添加“彳”旁,“彳”本象道路之形,进一步强化了“往”的行走义。隶变过程中,“往”字逐渐形成今天的写法。“往”和“来”词义相反,意为去往、离开,与说话人的距离逐渐变远。《诗·小雅·小明》“昔我往矣”,郑玄笺:“往者,从此适彼之辞。”也就是说,“往”表示从这儿走到那儿。与“来”类似,“往”由空间上的离去,引申表示时间的远去,因此“往”有“过去”之义。如《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强调对过去的释怀与对未来的把握。此外,“往”还可以表死亡或死者义,如《左传·僖公九年》“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杜预注:“往,死者;居,生者。”当生命的帷幕悄然落下,对于魂归天国的逝者而言,这何尝不是一场以永恒为航程的远行呢? “来”和“往”意义相对,常常对举使用。如《墨子·非攻》“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以往知来”意为依据过去推测未来的事。在此基础上,“来”和“往”组合而成了“往来”和“来往”两个同素逆序的反义复合词。“来往”的产生年代相对较晚,使用频率也少于“往来”。来去、往返义较早见于战国时期楚人宋玉所作《神女赋》:“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后多用为交际义,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华阳夫人)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到近代还发展出了表概数的特殊用法,义同左右、上下,如《老残游记》第十四回:“总不到顿把饭的工夫,水头就过去,总不过二尺来往水。”最后一种用法是“往来”所不具有的。 与此不同的是,“往来”用例早在甲骨文中就很常见,如“往来亡灾”“往来唯若”等,主要用于贞问商王田猎、巡狩、战争等出行活动是否顺利。“往来亡灾”体现了对“出入平安”的安宁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社会的往来出行呈现鲜明的阶层分野:商王出行关联田猎、巡狩等统治或享乐行为,而平民离乡则多因徭役征戍,如征戍诗《诗·小雅·采薇》所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折射出的离愁别绪。正如《汉书·爰盎晁错传》所说:“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迁徙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习性,故土难离才是农耕民族的天性。农业社会对土地的根植性依恋,加上古代交通条件下人员物资流转的低效高危,使得往来远行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死考验。这种集体焦虑也投射在民俗信仰上,如睡虎地秦简《日书》总计423支竹简,其中涉及出行禁忌的多达151支。通过对“远行”“久行”“长行”的术数规训,将空间位移的不确定性风险转化为可操控的仪式行为,本质是农耕族群在定居本能与迁徙诉求间的文化调和。 “往来”一词的语义范畴远超出单纯的空间位移,除从空间范畴向时间范畴拓展外,还进一步抽象化,渗透至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包括人际交往和精神交流等。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援引先秦古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揭示了人类活动背后经济利益的原始驱动力;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句,则将“往来”提炼为社会阶层交往的符号标记;至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更以诗性笔法将创作过程诠释为情感与物象的双向馈赠,完成了从物理位移到精神对话的升华。“往来”的语义演变始于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移轨迹,却在认知拓展中沉淀出超越具象的哲学意蕴,终成贯通时空、交融物我的精神远航。 (作者:孙 倩,系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