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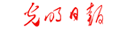
|
|||

|
|||
|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无不渴望自己的居所中能有一个单独的空间作为书房,在那里读书写作,驰骋思绪。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句“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晓开”,即彰显了文人对书房的挚爱。 回望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众多文学家笔底生辉,写下彪炳史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许多并非出自富丽堂皇的书房,而是写于被称作“亭子间”或类似亭子间的斗室之中。所谓“亭子间”,原指上海石库门建筑的一部分,诞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亭子间一般建在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正房后面楼梯的中间。七八平方米的空间,狭小阴暗,冬寒夏热,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作为佣仆的住所。旧中国,贫困的市民和小商贩常在此栖身,许多作家也散住于此。 鲁迅初到上海时住的就是亭子间,他的《且介亭杂文》就是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亭子间完成的。当时,在附近的亭子间里,还住着叶圣陶、茅盾等人。鲁迅所住的大陆新村,和瞿秋白住的亭子间仅隔一条马路,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文艺,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在这里写出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12篇杂文,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巴金曾把自己在亭子间的生活写进小说《灭亡》。周立波在1935到1937年间写过许多文艺评论,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亭子间里》。茅盾当年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缉住到景云里,整日隐居,足不出户。正是在这里的亭子间,他第一次以“茅盾”为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方寸之间的亭子间里苦中有乐,蕴含着人生的理想,从而形成了“亭子间文化”。 回忆过往,我也有过自己的“亭子间”。那是1978年初冬,我供职于政府机关,已娶妻生子,还没有固定的住房。为了解决无房户的困难,机关独身宿舍中辟出了几间房,作为年轻夫妻的临时住所。我住的那栋楼属临街建筑,当年楼房设计者为了街容美观,在三楼正中设计出一个尖顶。分配给我的房间恰巧在尖顶下方,这就使得我除了分得一个房间,又多得了那个尖顶小屋。那间小屋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对我而言可以说是绝好的书房。迁居后我高兴极了,当天就在小屋里摆下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一个两米高的书架,把当时自己仅有的一百来册图书全部摆上。其时,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已开始文学创作。每天晚饭过后,待家人熟睡,我便只身进入自己的“领地”读书、写作直至深夜,节假日更是足不出户。那时,当地的报纸副刊有一专栏,专发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每周一期。刊发前遇有稿件不济之时,编辑便会在头天下午给我打来电话索稿,要求翌日早晨上班前务必交稿。往往是接过约稿电话忙完工作后,草草吃过晚饭,便进入我那“亭子间”埋头写作。那时身边并无打字机,稿件写成后为留底稿,还需用复写纸抄写两份。这样忙完之后,窗外的街灯已经熄灭,东方甚至显露出熹微的曙色。一年半之后,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两室一厅一厨。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然而我也失去了自己的“亭子间”。事后每每想起还有怅然若失之感。一年半的时间里,寒暑易节,在那个鸽子笼似的空间里,我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部散文集的大部分篇章,计二十多万字。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退休,诸多文友常常来到我的书房、工作室共同切磋创作事宜。随着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文友们也几乎都有了自己的书房。我们时常抚今追昔,聊起早年前辈作家的亭子间经历。 一次,有位文友收到某刊物的稿费后,在一间很小的夫妻店请大家小酌。小餐馆举架较高,就餐的餐厅算是厨间上方辟出的一个房间。坐定之后,几位文友突然察觉到,此餐厅的大小和所处位置极像亭子间。于是,前辈作家当年在亭子间的写作经历又一次成为谈论的话题。还有人提出,建议店主人把店名改为“亭子间饭店”。听罢我们的议论和建议,店主小夫妻十分赞赏。此后,文友们不但常来此聚会,还热心地协助店主谋划“亭子间饭店”的改造事宜,演绎了一段与亭子间有关的佳话。 (作者:王本道) |